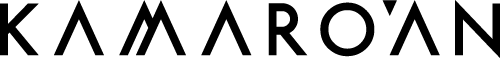器物是他們走過的歲月
text & photos by @hali_sawmah_
田調對象:Kacaw 陳彩生
地點:台東成功 Madawdaw 部落
紀錄者 sawmah a’do
這次來到小蔣 @lafa_angay 位於台東成功的老家,初次見面,被這個一家都看起來相當年輕的家族驚艷到了!
一陣問候與閒聊後,小蔣和伊麥從倉庫拿出了兩個正常大小的木飯桶 maho,阿公說,在阿美語裡,同樣叫做 maho 的器物有分兩種,一種是底部有挖洞,專門用來蒸米的木桶,另一種則是底部厚實、無洞的搗米桶,通常用於搗米殼或是蒸熟的糯米 hakhak,使之作為麻糬 tolon 食用。
這時小蔣媽媽提到,倉庫裡還有更巨大的 maho ,我們進到倉庫後,果然發現大大小小的 maho,我們驚訝的看著這些木桶,不經好奇起 kacaw 阿公的家族究竟有多少人,據說最大的木桶一次可以製作三到四十人份的糯米,不過阿公說,並不是每一次都會將糯米搗成麻糬,麻糬的製作相當耗人力,通常是男女婚娶時要準備的食材,在那個男方入贅女方家的年代,若婚娶時女方未準備麻糬,是有可能不成婚事的呢!
講到 maho,一定會好奇是如何製作的吧?kacaw 阿公說,製作 maho 必須從一根完整的木頭開始,慢慢以鐵製工具挖洞、雕刻,而這些木材的來源,大多都來自東河,『 東河的路邊很多樹!』kacaw 阿公這麼説。 負責蒸米的 maho 比較特別,因為內部有個讓蒸氣可以通過的洞口,為了不讓米粒掉下去,會再另外用竹片編製一個擋片,kacaw 阿公家製作的擋片也是很講究美觀呢!是以竹片為底、鐵絲編成,至於為何不是使用藤編呢?『 因為鐵絲比較耐用啊!』kacaw 阿公的太太說。
接著我們注意到一旁放著的、看似斗笠的藤編器物,相信大家拿到它的第一個反應動作,一定都是將它戴到頭上吧!Kacaw 阿公和他的太太看到我們將它帶到頭上,都不禁笑出聲來,『 那個是 maho 的蓋子啦!』他們說,『 哇!真的嗎!』身爲山線阿美族的我十分驚訝,自我有記憶以來,看過的蒸桶蓋不是木製的,就是早已現代化的鐵鍋蓋,未曾看過使用黃藤製作的蓋子。仔細觀察了一下,心中對於這個工藝手法冒出無限個讚嘆,為了讓蒸氣可以好好的鎖在藤蓋中,這些藤編的密度十分細緻,且編織力道一致,各個角度觀察到的曲線都相當平整,比起常見的平面編織,錐形和方形這種比較特殊的編織,肯定需要在編織時隨時調整角度,否則難以塑形。
接著看到的是,與蒸桶蓋形狀相似,但多了一層竹片底座的藤器,『 這個用做盛裝食物的 』 kacaw 阿公說,『 真的好像盤子! 』我心想,端詳著這個特別的形狀,我和 imay 在一旁討論著,『 妳覺得這個有可能是受漢人的文化影響嗎?』我問,『 很有可能呦 』imay 想了想後回答,『 為什麼它要再多加一層藤呀?是因為要用來盛食物,所以需要多一層支撐嗎?還是是為了美觀呢?』我又問,『 當然是用來多一層支撐呀 』imay 說,『 這個好像是成功這邊特有的形狀 』有著一半成功血統的 imay 說。
我看著手中的藤盤,好想搭時光機回到過去看看,好像所有知道肯定答案的人都已經離開了。
『 以前學習的就是這樣,所以我們跟著做 』kacaw 阿公說。我突然注意到所有邊緣是圓形的黃藤器物接口,似乎與方形器物的有所不同,圓形器物在邊緣接口上的『 藤 』,都會特別剖半後繞成圓形,再用另一半的『 藤 』相互貼合繞成完整的『 邊 』,最後以削薄的細『 藤皮 』將兩層或三層剖半的『 藤 』編織並加以固定。而方形的便當盒則不同,是以一『 藤 』到底的固定方式,僅在四個轉彎處做切口,最後再以『 藤皮 』做固定。
我問了坐在我身旁,十分擅長藤編的 imay『 為何圓形器物的邊緣要特別剖半呢?』,『 因為用完整的藤作為圓形藤器的邊緣,使用久了很容易變形或斷裂,器物就無法完整保存啦,方形的結構比起圓形來說更少拉扯,所以一藤到底就可以了! 』imay 這麼說。
多虧 imay,我得到一個心服口服的答案!
現代材料與舊器物的共存 — 尼龍繩與玻璃絲
『 我製作的同時也修補它們。』kacaw 阿公的太太說
近代,製作傳統器物所使用的材料,在取得的方面越來越不易(因人力與資源的匱乏等),以至於使用現代材質代替製作與修補的傳統器具越來越常見,上面三張的魚簍及籃器便是其中的例子。
回部落生活一陣子的我也察覺了這場時代的更替,看著這些『 新的器具 』與正在消逝的傳統文物,心中不免引發惆悵,這些器物依然保有它原有的形狀,但在本質上卻有所不同,我們身處於一個快速發展的時代,或許這必定會成為器物們將來會發展成的其中一種面貌,而這是無法避免的,如同世間的情感一般,我們這一代的人類,終究會少那麼一份存在在這個世界上的溫潤。
『 阿公、阿嬤會想用什麼更好的方式安頓這些文物嗎? 』在訪談的最後,tipus 開口這麼問,kacaw 阿公與他的妻子並沒有給予直接的答覆,但,他們眼神中剎那的一陣混濁,僅道出想好好珍惜這些寶貝的堅毅,對 kacaw 阿公與他的妻子來說,這些器物是他們走過的歲月,那麼,對我們來說呢?這是我成為工藝師以來,一直擁有的疑問,至今沒有一個發自內心覺得合適的答案,我深知傳統器物的美麗與珍貴,但未曾長久體會過與它們相伴著生活的溫度。
『 一定是還不夠久 』我的腦海中憶起那個翻開文物時,因灰塵過敏而打噴嚏的模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