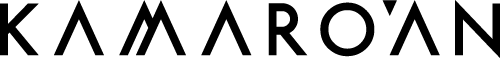4 - 生活中的意境與美學
「中國自古以來的哲學思想一直站在制高點上,尋求人與自然、個體與群體的整體和諧,這是西方所沒有觸及的宏偉氣魄」德國哲學家黑格爾是這樣形容東方哲學的,「但是東方對無限的追求,最後卻只得到了一個虛無縹緲的無限」[1]。
希臘的哲學奠定了西方思考模式的基礎,數學、物理、美學科學都是在哲學底下壯大之後才獨立出來的領域,其奠定者蘇格拉底沒有留下一字一句的著作,他的思想與學說都是由門生所記錄下來的。從人類發展使得宏觀視野來看,人類的進化是很奇妙的,幾乎是同一時期的中國,只約略早了蘇格拉底八十年,廣收三千多位門生的孔子誕生了,孔子以仁為美德的儒學同樣深植於中國近三千年來的主流思想之中。孔子的仁是世界大同的理想,也是君子的人格境界[2]。論語形容君子應當是文質彬彬的,文代表的是人對外待人處世的修養,質則是內心的本性與道德精神,論語尋求的是一種過猶不及的中庸之道,是以如果你汲汲營營於外表的形式便太過虛偽,而太過順著自己的本能忽略了世俗的規範的話就又過於野蠻,因此唯有形式與內涵表裡如一時,才是君子的人格美德。
我們可以發現孔子對於人格之美的理念是精神上的哲學,如果人們心中存有從內順從良知良德,從外保持人群和諧的平衡而協調的想法,這樣的精神體現在君臣父子倫理之中,也可以反映在鄰里相處之間。例如「禮之用,和為貴」說的就是即使我們在社會中有禮法可以遵從,但是你的心中也要存著和氣待人,替別人著想的心思才是提升社會運作的理想狀態。
而另一方面,在百家爭鳴的春秋戰國時代,對道家來說,美則是順其自然而無為的,這一點我們可以先簡單的從中西方對於無限空間的態度看出差異[3]。例如西方為了一窺極限的究竟鑽研數學、鑽研技術以發明望遠鏡[4];老子則認為大象無形,人生當如「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然不能至,而心嚮往之」,平靜地接受世間萬物運行的道理,從容地與之相處。
這樣的處世哲學也在中西方的繪畫之中的差異透露出端倪[5],例如西方醉心於透視法的結構,今天在義大利達文西的博物館中,我們仍然可以看見達文西為了作畫所製作的透視工具,或者在即使已經有抽象概念的印象派畫家梵谷與莫內的畫中看見透視記號的標記。中國的繪畫則很少呈現無限的空間,或是一望無際的畫面,我們通常會先看到雄偉的高山、枯木與環繞的雲霧,再順著山峭間的流水視覺向下,湖面上小船及水鳥,然後才是岸邊隨風搖曳的花。這也像是詩詞中詩經「蒹葭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溯洄從之,道阻且長。溯游從之,宛在水中央」,或是唐詩王維「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那種餘韻繞梁的空間感,這是專屬於中國言盡而意不止的美學意境[6]。與此同時,老莊的的思想更被體現在生活的價值觀之中。是以中國的人們往往能忍受暫時的失敗,靜待時機的到來,相信在天地萬物的體系中,在大自然生生不息的規律運作之下,終有時來運轉的一天[7]。
中國的美學家宗白華(1897-1986)認為,是四時的遷移輪替與四方東南西北建構了中國人的時空概念,也就是中國的宇宙[8]。也因此畫家與詩人對萬物的表現不拘泥在具象空間之中事物的排列,總是偏好在創作中帶入時間流動的節奏。中式畫家將時空視為一種渾然天成的體系,每件事物都擁有許多不同的面向,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混沌而圓融,是以多重視點往往同時出現在同一個空間裡頭,這也是中式繪畫掌握整體事物的鳥瞰法與西式定位定向的透視法不同思維之處[9]。
或許亂世不只提供了英雄豪傑發揮的舞台,更促使各地文人重新思索人生的意義。戰亂的生靈塗炭瓦解了過去的傳統、功業與信仰,曹操頌吟的「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象徵了人們開始否定外在權威與社會價值,轉而追求內在人格的覺醒[10]。人生在世的意義浮現出來,人們開始自覺個人才情、風貌、個性才是美的價值[11]。
中國的美學於是在漢代末年與繼之而來的魏晉南北朝中以獨立的價值與孔子的社會之仁、老子的世界之道分離了出來。例如世說新語津津有味描述的不再是忠臣烈士或是聖賢棟樑[12],而是玉樹臨風又飄逸瀟灑的文人,譬如容止篇形容嵇康風度容貌特別秀美,又清朗挺拔,或是在雅量篇描述嵇康在被行刑前,只留下廣陵散今絕矣的無所畏懼[13]。在魏晉的世代,人們欣賞人格之美,也讚頌個性的價值,我們也可以看見魏晉的審美觀對後世的影響,例如中國對藝術之「品」的評斷並不侷限在藝術上的造化,創作者的品格也往往為其作品帶來更多的價值,美被看作是與作者精神、氣質、心理不能分離的東西[14]。是以在想起李白之詩時我們會讚嘆他的灑脫之氣,在憶起杜甫之詩時我們也會對他的社會關懷肅然起敬,岳飛的滿江紅與文天祥的正氣歌雙雙因為其正義凜然的人格而被視為上乘之作。同樣的審美準則也被應用在魏晉的九品官人法中,例如選才選賢當以品格、才能為主[15],而非唐宋科舉或是明清八股文的學術檢驗。
當然,九品官人法在後期淪為世族壟斷的工具是後話了,這裡想說的其實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思維方式,喜歡將信奉的哲學從自身開始推己及物,小至一篇詩文,大至山河社稷都被看作是渾然一體系統[16]。
到了中國經濟、商業、人文藝術都發展到巔峰的唐宋,中國的美學轉向以作者因為外在的一山一景、一花一葉心境的轉折詮釋出了美的含義,作為美學的最高境界[17]。例如李白在將進酒中高吟「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君不見高堂明鏡悲白髮,朝如青絲暮成雪」,在宣州謝朓樓餞別校書叔雲中感嘆「抽刀斷水水更流,舉杯銷愁愁更愁」,或是辛棄疾「而今識盡愁滋味,欲說還休。欲說還休,卻道天涼好個秋」,蘇軾在竹林中「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心境平靜的意境。甚至今日俚語裡頭「如是心中無掛累,食葉飲水也會肥」也傳遞了庶民生活中清心快樂的自在。
走過了紛亂的遼金之亂與蒙古統治的元朝再到平民皇帝朱元璋的崛起,過去的書香世家[18]已近解體,不再有菁英階級的統一美學,晚明清初的文人不再借物寄情對人生展開反省思索,而是以個人的意識追尋生活中的真,以人情、物理、世故來表達自己對生活的體悟與獨到的見解[19]。這其實跟今天每個人都在追尋屬於自己的生活風格是有點類似的,例如人們總是懂得杯中喝的是何處產的帶有清新花果香的咖啡,對爵士樂的如數家珍與對紅酒的鑑賞能力是那樣的展現了你的生活品味。
另一部分的原因則是因為前朝詩詞書法的造詣已經幾乎達到寫意的巔峰,寄物寓意的極限,於是文人開始從庶民文化之中取材,日常生活的各種瑣事在他們眼中也變成別具風味的生活情趣。文人取材廣泛又隨意書寫,小而質輕的小品文有如作者對生活的隨手點評,例如張潮在《幽夢影》中曾寫道「花不可以無蝶,山不可以無泉,石不可以無苔,水不可以無藻,喬木不可以無藤蘿,人不可以無癖」、「楷書須如文人,草書需如名將,行書介乎二者之間,如羊叔子緩帶輕裘,正是佳處」或是「新月恨奇易沉,缺越恨其遲上」。悠遊在生活之中的輕鬆筆觸讓中國的文學終於不再侷限於仕途不順、憂國憂民、抑鬱寡歡、有志難伸的感慨,解放了文以載道的沈重傳統。
林語堂(1895-1976)在以英文撰寫的《生活的藝術》中不遺餘力的將張潮的幽夢影傳入西方的世界,他也提到他贊成一切的業餘主義,因為業餘[20]永遠是自主尋找生活之中的樂趣的精神,人們為了送朋友而寫的歌、週末沈醉在院子裡的養花趣味與旅行中的攝影總是最有感染力的,因為藝術的靈魂是自由的[21]。
值得一提的是,在過去的時代,「雅」象徵的是高位、清逸與崇尚,「俗」代表的則是與大眾水平保持一致、樸實而簡單的風俗民情,明朝階級的解構讓雅士需要俗趣,俗子也想領略清風明月的意境,形成一種雅俗共賞的情趣[22]。俄國巨擘小說家托爾斯泰最終也走入了雅俗共賞的境地,他認為為了藝術應當是為了人,為了與社會大眾溝通的目的而創作的,因此他在晚年時鄙棄自己的巨作《戰爭與和平》,轉而喜愛早期寫成的淺顯易懂短篇小品。
從春秋戰國、魏晉南北朝、唐宋盛世到晚明清初,文人雅士在創作上的追求在文以載道、清風談吐、心境反思、或是生活情趣之間來回擺動,但是自始自終貫穿於詩詞書畫琴棋生活之間的都是意境二字。意境其實跟接受美學的概念是很相似的,兩者都是自客觀事物、文化社會背景與主觀思緒之間的互動關係,情景交融之下所產生的美的感受[23]。中國的美學一直以來都是以觀者為本的,唯有我們在欣賞嵇康的瀟灑所啟發的欣慕之情,蘇軾的蕭瑟所引發的空寂感受,或是岳飛的激昂所喚起的熱血沸騰時,意境才由觀者心中所產生超越語言的層面而延伸出的無窮意涵,在寄託了作者情感思想的同時也啟發了觀者的情感思想,創作的價值方於是焉成立。
✦本文作者為Kamaro'an設計師張雲帆 / 歡迎分享連結 / 未經允許請勿轉載
[1] 劉綱紀,《傳統文化、哲學與美學》(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6),237。
[2] 宗白華,《美學散步》,65-69。
[3] 同前註,58。
[4] 其實中國同樣對星象有著濃厚的興趣,但是由於星象在戰國時期因鄒衍的五行說與天命連結了起來,自漢朝以降朝廷便規定只有欽天監可以觀測星象,百姓私下紀錄星軌者格殺勿論,而少數的欽天監則使星象知識時常在改朝換代的戰亂中遺失,是以中國歷來曾發展出無數不同款的渾天儀。
[5] 宗白華,《美學散步》,52-55。
[6] 同前註,19。
[7] 林語堂,《生活的藝術》(台北:遠景,2003),125。
[8] 同註60,51。
[9] 同前註,149-151。
[10] 同前註,71。
[11] 李澤厚,《美學.哲思.人》(台北:風雲時代,1989),113。
[12] 李澤厚,《美學.哲思.人》,116。
[13] 宗白華,《美學散步》,72。
[14] 林語堂,《生活的藝術》,355。
[15] 劉綱紀,《傳統文化、哲學與美學》,249。
[16] 黃俊傑,《東亞儒學史的新視野》(台北:財團法人喜瑪拉雅研究發展基金會,2001),318。
[17] 同註70,254;以及李澤厚,《美學.哲思.人》,149。
[18] 即使是科舉時代如唐朝,你的出身與家族還是對仕途或藝文成就很有影響力的,是以出身悠久舊世家的杜甫即使窮困潦倒仍然自豪的說「詩是吾家事」,晚唐的杜牧也很得意自己家中歷來所搜羅的古書都是最優秀的版本。
[19] 黃雅莉,〈依違於二元之間的中道和諧––張潮《幽夢影》創作模式下的精神內涵〉,《成大中文學報》,第四十五期,2014,205-249。
[20] 張潮在當時屢試不上,幸所幸家世底厚能在閒暇之餘開發許多興趣。
[21] 林語堂,《生活的藝術》,349-350。
[22] 關於雅與俗的更深入探討可參考中研院研究員王鴻泰,〈雅俗的辯證――明代賞玩文化的流行與士商關係的錯雜〉,《新史學》,第七卷第四期,2006年。
[23] 宗白華,《美學散步》,11-36;以及李澤厚,《美學.哲思.人》,1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