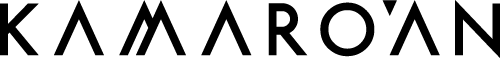就試試看,讓器物醒過來
text by @hali_sawmah_
photos by @hali_sawmah_ & @nacu_dongi
臺東成功 Madawdaw 麻荖漏部落 文物田調紀錄
田調人員:tipus / imay / nacu / lafa / sawmah
紀錄者:sawmah a’do
充滿女性力量的傳家寶 —— ‘asolo 與 tatalikan 沈甸甸的石杵與木臼
寒冷潮濕的冬季午後,imay 阿嬤從屋中緩緩走出,客廳中央的器物被一張大的透明塑膠布層層包裹著。孫女 imay 說:「這就是我阿嬤他們保存物品的方式,最直接、最簡單的樣子。」
打開塑膠布,映入眼簾的是一根極為美麗的石杵。石杵的中段用一根竹管及藤圈包裹著。
「石頭的部分好光滑呦!」大家驚艷地輪流傳接著手中的 ‘asolo。
「這是我婆婆送我的!」imay 阿嬤說。時間的流逝,讓這根歷史悠久的石杵變得如此溫潤。這時,tipus 提出心中醞釀已久的疑問:「阿嬤,妳的 ‘asolo 是一整塊完整的石頭嗎?還是用兩塊石頭拼接起來的呢?」
「兩塊石頭放一起,再用竹子把它接起來。」阿嬤回答。
這解開了大家的疑問——原來,要找到如此修長的石頭並不容易,大部分的長石杵都是用竹管連接兩塊經過打磨的石頭製作而成。竹管的上下均會切割出縫隙,使石塊能更好地卡入竹管,最後再用藤皮在竹管上編織固定,使其完整。
阿嬤還說,並不是隨便一塊石頭都可以製作成 ‘asolo。長型的石塊不好找,特別要到台東知本才更能找到合適的石材,因為那裡的溪很多。
imay 阿嬤雙手握著婆婆給的 ‘asolo,像是抱嬰孩那般珍惜。「我有請人製作一個木臼 tatalikan 來搭配這個 ‘asolo 使用,不過木材是我自己去揹回來的,很重呦!」阿嬤笑著說。
據她所述,每當颱風季過後,東臺灣的沿海一帶都會出現許多從山上沖刷下來的漂流木。而阿嬤便是在 2009 年的八八風災後發現了這塊木頭,並憑一己之力將其帶回。
聽完阿嬤獨自揹回這麼重的木材的故事,在場的每個人都覺得不可思議,但阿嬤卻一派輕鬆地說:「反正就這樣啊!我感覺它是很好的木材,就帶回來了。它跟我回家,就變成我們家族的家產了!」她的眼神閃閃發光。
無論是 imay 阿嬤,還是那來自婆婆的 ‘asolo,都能讓人感受到那強烈的、充滿力量的 Pangcah 女性在生活中的態度與生命的堅毅。
房子深處,沈睡的物件們 —— tahka、tapucong 與 maho 藤盤、藤蓋與蒸米桶
我們隨著 imay 阿嬤的腳步來到房子的後方,見到了家族流傳下來的其他寶藏。
阿嬤家的 maho 和 kacaw 陳彩生阿公家的 maho 一樣,一次蒸煮,便足以供養三至四十人一餐的溫飽,可見當時家族十分興旺。
阿嬤說,製作 maho 的木材可以有很多種,而他們家的 maho 是由一種叫做 kaliron、帶刺的樹木製作而成。這個蒸米桶外表雖然龐大,實際重量卻很輕盈,底部有個蒸米孔,與用來搗糯米的 tatalikan 木臼不同。
「這個現在還會用嗎?」tipus 問。
「沒有了啦!家裡人不喜歡吃糯米,說吃了肚子會胃脹脹,不好消化,我就不煮了。」imay 阿嬤說。
不過,事後阿嬤的孫女 imay 偷偷地說:「其實是因為阿嬤老了啦,我還很愛吃。」
我看著體積龐大的 maho,想像著三、四十人家族團聚的盛況。地上鋪滿一盤盤圓圓的藤盤 tahka,裡面盛裝著熱氣騰騰的 hakhak 糯米與 tolon 麻糬,耳邊彷彿傳來當年的喧囂。然而,如今這個老家裡,只剩下 imay 阿嬤一人居住在 Madawdaw,心中不禁湧上了一道惆悵。
「哇!這個帽子真的只有成功這邊才有耶!我們港口部落都沒有。」nacu 試著把藤蓋戴在頭上,逗趣的舉動將我拉回現實。
「對呀阿嬤!我們 kalingo(花蓮)的都沒有。」tipus 附和著。
「這些以後都是我的古董!」和 imay 阿嬤同名的孫女 imay 興奮地說著。
你們會不會做這個? —— 就試試看,讓器物醒過來
此時,一旁的 lafa 正安靜地觀察著阿嬤家倉庫裡的 fitay 篩網。專注的眼神,就像溪水繞過每一塊停留在水中的堅石,仔細地研究每個藤編的細節。
「你們會不會做這些?」imay 阿嬤問。
「如果不會的話,阿嬤讓你們帶一個 tahka 回去研究怎麼做。」阿嬤又說。
一股掩不住的興奮似乎在每個人的眼中流露,但伴隨而來的還是對器物保存的擔憂,畢竟這些僅存的器物,都是屬於某個家族的寶物啊!
我的目光率先落在孫女 imay 身上,發現她的眼睛裡有光,就像她的 mamu imay 一樣。
十幾年前,imay 阿嬤和她的婆婆在海邊找到可以製成器物的自然資源,而歲月的沉積,將它們變成家中珍貴的寶藏。十幾年後,這些寶藏成為我們在學習工藝路上的老師,正悄悄地用無聲的姿態,引導我們往回推溯它原來的樣子。